原文:Taste games
说明:翻译借助 AI,有基于译者本人「品味」的删改。
你一定不讨厌糖的味道,也必定会因为好看的人 get 到你笑点开心。是吧?我也一样。
但说到露营、音乐和快餐,奶酪、汽车、真人秀呢?有的我挺喜欢,有的则不大感冒——听起来还蛮自由意志的。不过如果你来猜猜我对哪些东西感兴趣,估计会八九不离十——这是为什么?
一种对皮埃尔·布尔迪厄的解读认为,我们喜欢某事物是因为喜欢它们对我们有利。品味不过是:
- 理解在社交环境中喜欢事物的后果,以及
- 掌握如何「正确」喜欢事物的文化知识。
你的大脑在运用博弈论:周围厉害的家伙们喜欢土豆吗?你喜欢土豆有好处吗?你已经了解土豆的消费仪式,足以融入热门的土豆沙龙了吗?那么:开始喜欢土豆吧。
令人不安的是,这大多是无意识的。我们是社会性生物,能感知到为了取得进步,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,然后我们就成为了那样的人,整个过程都不涉及变幻莫测的理性。
这靠谱吗?
好吧,先看看这个:

当我凝视这张照片时,很难觉得这件宽松的衬衫和牛仔裤「客观上」好看。鉴于我的品味,我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不喜欢它们。
但这显然不是真的,对吧?如果是 1993 年,我会觉得这些衣服没问题——就像其他人一样。如果是 1793 年,我想我会认为这个男人应该戴顶假发。
没办法——我不喜欢这些衣服的原因其实是:自 1993 年以来,时尚变迁,我已经将这些变化内化于心。我内化得如此彻底,以至于它们仿佛成了我不可更改的一部分。如果随意的文化波动能如此深入地渗透进潜意识,那么这一切将在何处终结?
或者,假设你明天女儿就要出生了。你更愿意给她取名 Pamela, Brooke, 还是 Ruby? 现在,来比较一下:

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,这些名字受欢迎程度的周期是由阶级驱动的:上层阶级的人开始使用不寻常的名字来表明他们孩子与众不同,随着人们试图模仿那些地位稍高的人,同时又与地位稍低的人区分开来,这些名字逐渐沿阶级阶梯向下传播。
我从未见过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种「姓名阶级决定论」确实成立。但我们往往会发现,当某个名字开始在同龄人中流行时,它对我们就变得悦耳起来,即便我们并未意识到它正在流行。因此,布尔迪厄似乎确实触及了某些实质。
豪华轿车游戏
过去几年,我惊讶地发现一些亲戚对昂贵的运动鞋着迷。我想,好吧,人们总会找到方式来划分社会等级。但通过购买如此昂贵的东西来较劲也太浪费了吧。
根据我们的理论,答案很简单:人们喜欢运动鞋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,喜欢运动鞋对他们有利。质疑为何他们不通过自己编织手套来竞争是愚蠢的,因为没有哪个人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人们只是遵循自己无意识的品味算法罢了。
就像对名牌运动鞋无感一样,我对昂贵汽车、金饰或名牌手袋也从未心动。我想可能我自认为有原则、深沉吧。但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下,我对这些事物的漠然态度完全可预见:我不喜欢它们,因为我的文化资本远超经济资本。
玻璃珠游戏
1943 年,赫尔曼·黑塞描绘了一群生活在数百年后的知识分子,他们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,玩着一种名为「玻璃珠游戏」的活动。游戏的运作机制并未被完全阐明,但其似乎要求玩家同时精通文学、艺术、数学、历史和科学,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越来越深奥的类比关系。
而我呢,或许会钟情法国跑车,闲暇时沉浸在布加迪的世界里。又或者,我会投身于功利主义,空闲时与人辩论亨利·西季威克的观点。为何我选择了后者?是不是因为(a)我如今乃至以后可能都没法拥有一辆布加迪,但(b)我在抽象概念的侃侃而谈上胜过多数人?如果我超级有钱但学识浅薄、缺少时间,我的追求还会相同吗?
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人玩豪车游戏,而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人则玩玻璃珠游戏。我们都在玩自认为能更胜一筹的游戏。
贬值游戏
但我认为还远不止于此?
我估计在关于「意识是什么」之类的的辩论中可以赢过唐纳德·特朗普。但在「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于各处豪宅,由模特喂食鱼子酱」的比赛中会完败。
或许,特朗普和我能认定彼此不同的地位追求策略没有冲突,因此互不干扰。然而,我们似乎并未如此行事。实际上,像我这样的人会嘲笑镀金马桶,坚称我们真的真的真的对这类事物毫无兴趣,我们无法拥有它纯属巧合,还是来继续讨论法国大革命吧。
而像特朗普这样的人,在我想象中,会认为像我这样 loser 们,因为不能在真正的游戏——唯一真正重要的游戏里获胜,因此绝望地发明了虚假的智力游戏作为抵抗,
我认为花费 250 美元购买名牌运动鞋是「浪费」的,因为我并不看重名牌运动鞋。但「浪费」是一种价值判断。考虑一下玻璃珠游戏爱好者喜欢的活动,比如研究范畴论或撰写 18 世纪秘鲁水果价格的专著。玻璃珠游戏类型的人可能会辩称这些活动是富有成效的,并不消耗资源。然而:
- 你撰写那部专著真的是因为你认为它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吗?还是说只是想炫耀下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本?
- 时间是一种资源。投入到玻璃珠游戏上的所有努力本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。
所以什么都可以是浪费,只是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有价值。
幕间休息
这是一幅静物画,描绘了一只酒杯,因为我想用它点缀下这篇文章的大段文字,以及/或者想提升我的文化资本形象:

旅行游戏
你看到人们在炫耀什么?对我来说,是旅行。
我一直对人们谈论旅行的方式感到不舒服。毕竟,旅行开销不菲。在我的圈子里,没人会想在派对上炫耀他们的新劳力士。但不知为何,旅行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炫耀性消费,却不受炫耀性消费的约束。
为什么?
我的阴谋论是,旅行之所以迷人,是因为它融合了「豪华轿车」与「玻璃珠」。在我认识的人里,没人炫耀乘坐头等舱前往迈阿密四季酒店的经历,因为那纯粹是「豪华轿车」——你只需支付费用即可享受。而真正的旅行游戏,则需深入世界某个不寻常的角落,体验陌生的文化,掌握当地语言,结交当地朋友,探寻隐秘的地下派对,夜闯古堡,品尝 18 世纪僧侣酿造的醋。
即便你专注于展示丰富的文化资本,旅行依旧需要金钱。更深层的阴谋论认为,旅行之所以流行,是因为它为那些在社交上不被允许玩「豪华轿车游戏」的人提供了一种途径,让他们可以假装只是在玩一场普通而体面的「玻璃珠游戏」。
逃脱游戏
我强烈推荐布尔迪厄给那些寻找神经质新素材的人。在研究这一切的过程中,我偶然在一些论坛上看到人们讨论倒气泡酒的正确方法。主要有三种观点:
- 倾斜玻璃杯。
- 不要倾斜杯子。
- 随心所欲吧,别这么没安全感,天呐。
谁是对的?
第三个选项看似有力。但我注意到:没有人只是简单地说做你想做的。他们总是先表明自己理解关于倾斜与否的标准论点,然后才说可以忽略这些论点。
谁缺乏自信?
真正人道的立场或许是承认我们都有不安全感,因此即便你觉得葡萄酒的尊贵地位荒谬,想要了解那些标准论点也无妨。传统上,葡萄酒直倒是为了让管家不必从桌上拿起你的杯子。过去人们认为直倒——或许辅以某种特殊技巧——能更好地保留气泡。但你并无管家,而倾斜倒酒实际上能略微更佳地保住气泡。无论如何,差异微乎其微,谁又在乎呢。用这样的知识武装起来,就可以抵御任何可能试图削弱你社会地位的人了——随心所欲去做吧。
在撰写上一段时,我脑海中涌现出一些想法:
- 我需要解释关于是否倾斜的标准论点吗?
- 读到这里的任何人都会想知道,对吧?
- 还是说我只是在自欺欺人,因为我想要找个借口来展示我了解这些论点?
- 还是说,我所谓的「真正人道立场」不过是一种企图,想把自己置于那些主张第三种选择的人之上——正是我指责他们所进行的那种地位争夺?
- 我在这里究竟想达成什么?为何要写这篇论文?我这辈子都干了啥?我是谁?
显然,许多人在阅读布尔迪厄时会有类似的反应。这是一种看待世界的非常奇怪且令人不适的方式。
艺术游戏
在接触布尔迪厄之前,我将当代艺术视为无辜且易懂的。随心所欲就好!没有规则束缚!有时在博物馆里,我会经过那些几乎只是单一纯色的画作,比如阿德·莱因哈特的《Ultimate Painting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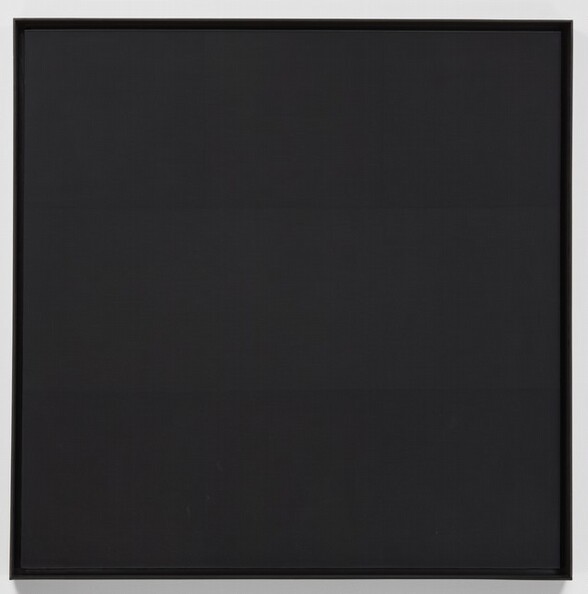
我几乎不屑一顾,心想:「或许几十年前这还有点意思?」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这类艺术在尝试挑战观众,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放轻松些。
听起来不错。然而读过布尔迪厄之后,我发现自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:
- 艺术博物馆里满是迷人、穿着得体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,这仅仅是个巧合吗?
- 既然你这么喜欢艺术,那为何不在家多看看艺术书籍呢?
- 你说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。但人们怎么知道不该把事情看得太严重?
- 你确定不享受轻触那些纯色画作的瞬间吗——置身于一个充满不言而喻的规则与模式的环境中,而你已积累足够的文化资本,足以让你悠然自得地告诉自己,这里其实毫无规则束缚?
布尔迪厄同样花费大量时间探讨艺术生产,将其视作一个巨大的战场。艺术家们为争夺地位竞争激烈,以至于常常绞尽脑汁寻求更显上流阶层的方式。因此,他们偏爱的一种策略是从下层阶级中汲取风格。尽管他们可能会穿着为工人设计的服装,但绝不会选择马球衫或卡其裤,因为这些被视为中产阶级的标志——存在太大风险,竞争对手可能无法领会他们的高级技巧。
啤酒游戏
我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类比。比如,我有时会买高档啤酒,有时则选择便宜的大众啤酒,但从不碰中档啤酒。有时我还会带着我最爱的美国大众啤酒去参加派对。(请注意,是真正的大众啤酒——百威蓝带是给装腔作势的人喝的。)这样做时,我认为自己是在拒绝被他人愚蠢的地位驱动观点所左右。我专注于啤酒的实际口感,因此我能看出我的啤酒比其他人喝的中档欧洲或亚洲啤酒要好得多。其他人对此视而不见,因为他们已被灌输了大众美国啤酒天生低档的观念。
我确实这么想过!但为何我从未发现一款「真正美味」的中档啤酒呢?
更糟糕的是,有时别人对我喝的东西嗤之以鼻,我内心的一部分会想:「哈!他们以为自己带了波丁顿就很不错了。波丁顿!哈哈!他们在等级体系中太低了,甚至没意识到我比他们高。哈哈哈哈!」
至少,我觉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?在某种近乎无意识的状态下?我在这上面花的时间越多,就越难回忆起来。
沃霍尔游戏
若你对品味游戏感兴趣,那么安迪·沃霍尔 1977 年自传中的这段文字,可谓奇异至极:
这个国家的美好之处在于,美国开创了这样一个传统:最富有的消费者与最贫穷的人购买的基本是同样的东西。当你在电视上看到可口可乐,你会知道总统喝可乐,伊丽莎白·泰勒喝可乐,想想看,你也能喝可乐。可乐就是可乐,再多的钱也无法让你喝到比街头流浪汉手中的那瓶更高级的可乐。所有的可乐都是一样的,所有的可乐都是好的。伊丽莎白·泰勒知道这一点,总统知道这一点,流浪汉知道这一点,你也知道这一点。
在欧洲,王室贵族与农民的饮食天差地别,他们的食物截然不同。要么是山鹑,要么是麦片粥,各阶层固守着自己的食物。然而,当伊丽莎白女王访美,艾森豪威尔总统为她买了一个热狗时,他肯定自信满满,认为女王在白金汉宫收到的热狗,绝不会比他在球场花可能仅二十美分买的那只好。因为球场热狗无与伦比。无论是一美元、十美元,还是十万美金,都无法买到比这更好的热狗。只需二十美分,人人皆可拥有。
有时你幻想那些高高在上、富甲一方、生活奢华的人拥有你所没有的东西,认为他们的东西必然比你的好,只因他们比你更有钱。但他们喝同样的可乐,吃同样的热狗,穿同样的 ILGWU 服装,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和电影。富人看不到更滑稽的《Truth or Consequences》,也看不到更恐怖的《驱魔人》。你同样可以感到厌恶,同样会做噩梦。这一切,其实都很美国。
基本上,他说:「美国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我们废除了品味游戏,品味不再代表阶级,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最好的,太棒了!」
他错了,我们不必浪费时间争论。但他真的相信吗?1977 年,这对美国而言比对欧洲更真实吗?沃霍尔是否已攀登品味之梯至高,以至于整个游戏对他而言变得不可见?他是否在玩某种元游戏,通过否认品味游戏的存在来戏弄所有人?
显然,美国总统请英国君主吃热狗是一种传统。1939 年,罗斯福在家中招待伊丽莎白女王时,据说她询问如何食用热狗,罗斯福回答道:「非常简单,把它塞进嘴里,一直推直到全部吃完。」
然后呢?
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理论难以证伪:你认为自己没有玩品味游戏?你认为自己「真的喜欢」某些事物是因为它们的特性?那是因为你在玩更高层次的游戏!
这一切被认为是无意识的,倒是相当方便。
还有一种奇怪的负罪感:如果你刻意改变自己的品味以融入群体,那是不好的。如果你无意识地这样做,那就更糟了。如果你无意识地不去尝试融入,你就是人渣。
同时,品味游戏本就是人之天性。布尔迪厄本人多次指出,试图逃避这些游戏是不可能的。若此言不虚,我们又何须感到内疚呢?
类比而言,你或许会认为,尽管渴望拥有孩子看似是对新生命的爱与呵护的向往,但实际上,这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基因自私复制的欲望。对此,你是否应感到内疚呢?这种观点颇为罕见。大多数人认为,无论起因如何,他们对孩子的爱是真切的,为何要反常地追溯因果链,试图将一切变得如此阴暗呢?
同样地,如果品味游戏是人的天性,那我们为何不接受它呢?显而易见的区别在于,对孩子的爱能产生积极结果(未来有更多被深爱之人),而品味游戏似乎带来负面影响(加剧阶级分化,减少社会流动性)。
所以,我并没有一个绝佳的答案。品味游戏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模型。但如果我们身上真的存在这种决定我们喜好的无意识程序,那么我们或许无法克服它,也可能本就不该去克服。
客观来看,或许性和排便令人反感。但健康的人不会抗拒这些本能,因为它们是人之常情。我们能做的,就是对此保持幽默感。或许对待品味游戏也应如此。(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另一种游戏——那就打住吧!)